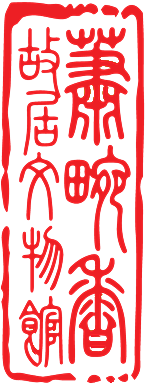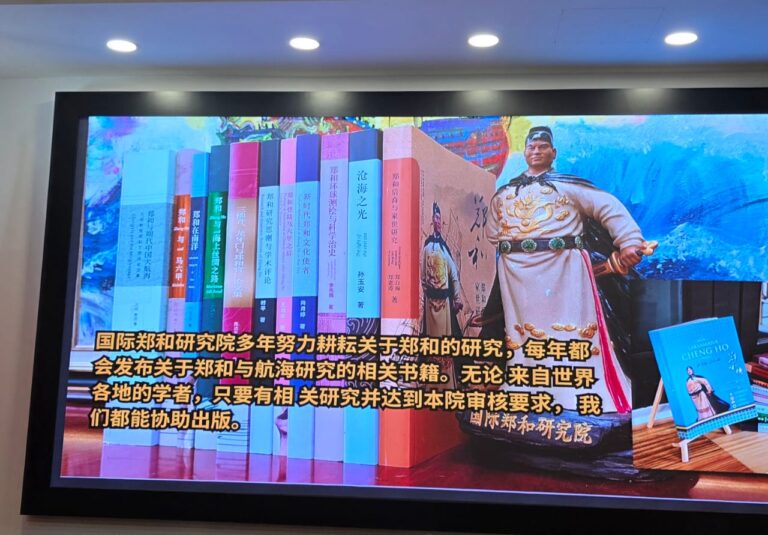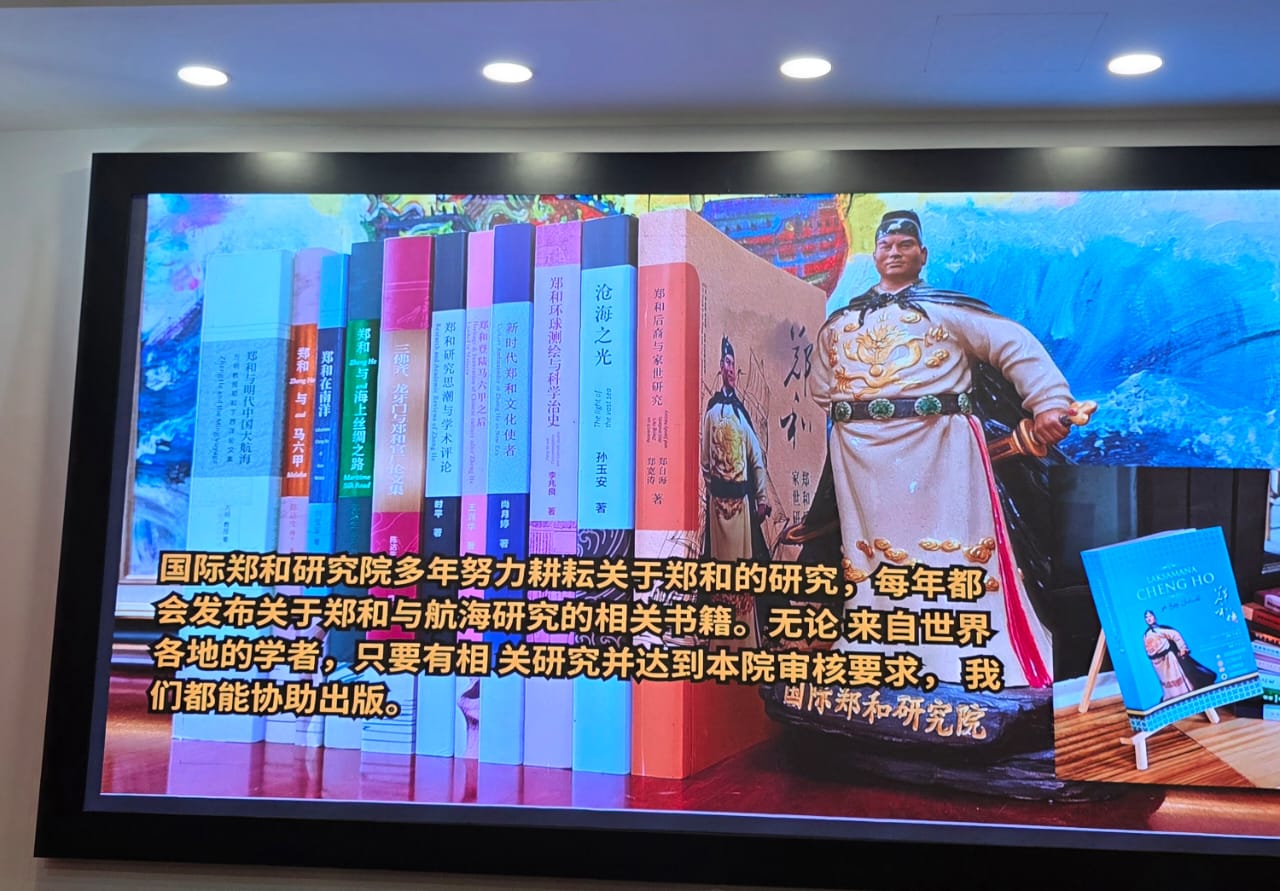作者: 安焕然
作者: 安焕然
在海拔800多米的大帽山山脚下,有个叫进光的小村落(旧称箭管、进灌)。那是一个道地的大埔客家山村,穷乡僻壤。昔时,一些大村落的装神送鬼者,念符咒及驱赶魔鬼送至三岔道时,嘴里喃喃念道:「要米要谷,去横溪水竺;要茲要粄,去文峰进灌。」将鬼怪也送到这个边远的山区里来。
过去,进光要跟外面接触很不方便。开门见山,只能走山上的羊肠小径。有一年过节,进光村里一位8岁的小男孩,嚷着要跟妈妈到十余里外的湖寮镇葵坑村的外婆家去。母亲拗不过,带着小男孩开开心心、蹦蹦跳跳步行回娘家。哪知层峦迭翠,山路难行。回程路上,上坡下坡,汗流浃背,小男孩直嚷:「走不动啦!走不动啦!」母亲肩挑着外婆送给的蕃薯杂粮,也很无奈,埋怨:「叫你别来偏又要来,看你妈肩挑重担,想背也背不得你呀!这样的山间僻地,要轿没轿,要马没马,要识安乐,将来你有本事,开条车路来…
后来,这个男孩在18岁那年下了南洋。几十年奋斗,事业有成。为实现慈母当年的那一番话,自1984年,花了几年时间,果然独捐巨资修筑了一条全长24公里,途经进光村家门的湖光公路(从大埔县城湖寮,经葵坑、进光,到平原镇之三岗)。这条铺上柏油路面的公路共耗资人民币500多万,是大埔县第一条标准化的侨资公路。它的修筑,使进光北上县城湖寮,南下高陂镇连成一线,也为湖寮到高陂路程缩短了10多公里。
而这位独捐巨资的善翁,当年那位顽皮的8岁小男孩,他就是萧畹香。萧畹香(1902-2000),号兰轩,祖籍大埔湖寮进光村。 18岁下南洋,在马来半岛南端的柔佛新山发迹,创建和昌机构。生前,他不仅在家乡祖籍地大埔修筑村道、凉亭,兴建了百候医院、百候大桥,还为梅州嘉应学院、大埔高陂中学、百侯中学、华侨二中等30多间学校捐资,并在故乡独资创办进光中学。 1980年代至2000年,其家族企业对学校及各项慈善事业的捐资超过人民币2千万。
1991年,进光中学被列为大埔县重点中学,被评选为梅州市最具办校特色的20所中学之一。
1990年以来,该校高考升学率逐年增长,至1995年高考成绩录取率高达95%,居全县第一。
1996年进光中学更被评选为梅州市一级学校。
在大埔,处处有萧畹香留下的善举事迹。在进光,萧畹香更是莘莘学子敬仰的慈善伟人。当然,在这一切的慈善义举之中,也曾遭受种种不信任及顽固的阻力。萧畹香唯有以「岂能尽随人意,但求无愧我心」以自勉。
10年前(2003),我曾到大埔客家村落搜集萧畹香的事迹文物,受到地方党书记、大城县副县长和教育局官员等的热情招待。大埔传统客家菜强调「油」、「咸」和「烧(烫热)」。除了美味香滑的客家酿豆腐,选有蛇肉、狗肉、蜂蛹和「神雕」。有的敢吃,有的真是不敢尝试。对着满桌「佳肴」,我向大埔县副教育局长问说,过去萧老先生最喜欢吃哪一道菜?黄副局长想了想,说:「最初的一次,萧老来时,大家盛宴款待,那知吃到最后,萧老先生突然问:『可以不可以给我一碗白粥? 』当时餐馆根本没有准备,大家非常的尴尬。 」
又有一次,萧畹香在进光村小住几大。午饭,家人蒸蕃薯。大家频赞这蕃薯香甜好吃,惟独萧老默不作声地连同蕃薯蒂、蕃薯皮一齐吞落肚。在座的陪客家眷面对着各自桌前一大堆的蕃薯皮、薯蒂,哑然自悔。
过去,我一直不能理解祖父辈的祖籍「原乡」之情。这一次,来到客家大埔,走了一趟,欣赏着这里的山水,遥想当年他们沿着韩江顺流而下到汕头出海的情景,对于他们的情、他们的忆,顿时对一切都释怀了。马来西亚华裔几代人的故事,成长的历程,不管是情紧祖籍原乡,还是热爱马来西亚这块土地,我们要的不是虚胖的大中华中心主义,也不是无知地沉醉在「马来西亚.能」的口号里头。我们要的不是自轻自贱的奴颜个性,更不是盲从拜倒在色彩鲜光、霸气十足的西方围裙底下。我们要的,只是一份真挚的爱。手握泥士,她之所以芬芳,在于她的真,以及我们心中的情。
再说,虽说萧老情系大埔,但对于他奋斗的本士(马来西亚),也一样关心。南方学院的献地,宽柔中学几座教学大楼的建筑,他都慷慨过。尤其是在1960年代初期,萧畹香担任宽柔中学董事长。当时,宽柔中学董事会刚刚宣布不再接受政府津贴,成为全马第一所宣布不改制的华文中学。宽中董事会认为,今后有几个学生就教几个,一切不敷费用由董事会来承担。在备受压力的当儿,有人游说劝告宽中董事会还是改变初衷,接受改制吧!萧畹香激动地说:
「不能改制,不能改制。要改制,我就退位不做了!」
本文原刊于2003.12.7, 星洲日报.文化空间.边缘评论专栏; 并于 2013.2.11修订。